1981年5月,周思聪到四川大凉山访问写生。天赐良机,她发现了一片好像从来就属于自己的“领地”——彝族妇女和她们的生活情状使她深心触动,感到一种由衷的惊喜。她画了一批洋溢着灵感的写生。归来后,就在画《矿工图》的同时,她开始了彝族女子系列的创作。这一坚持了若干年的系列作品,标志着周思聪绘画的新阶段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40.5×242 cm
强烈的社会性主题转向了平凡的生活性主题,对庄严崇高的关注转向对平朴清隽的倾心,形式风格的朴茂浑厚也过渡为细腻俊逸。精神方面,则由直感人生深入到咀嚼人生。在此之前,她偏重描绘再现,情感强烈而单纯;在此之后,她偏重抒发表现,情感内敛而复杂。从《人民和总理》到《矿工图》,经历了把遮蔽着的个性敞开的过程,至彝族女子系列才回到个性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1
换言之,由整个文化环境造成的创作与气质自我相分离的状况,又因文化环境的变迁和艺术家的主动寻求而得以克服,趋于统一。在周思聪的艺术历程中,这是一次深刻的自我超越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2
彝族女子系列断断续续画了10年,画家的兴致未衰,好像不是周思聪捕捉了她们,倒是她们抓住了周思聪。但画家对她们的生活情景和喜怒哀乐的描述,实在也并不广泛细致,大抵是拾柴、收获、采果、放牧、携子、幽会等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3
与其说画家在不停地反映她们,莫如说在不断地借她们抒写自己的情怀。系列中常见的荷物女形象,就最为典型。荷物女(或曰“负重女”)最早出现在1981年春画的一件描绘藏族妇女的作品里,当时周思聪还未去大凉山。从大凉山回来创作的第一件重要作品《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》,画的就是两个背柴的彝妇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4
野旷无声,暮色苍茫,她们在归途中歇脚喘息,老年妇女坐地,中年妇女倚立,满面疲劳,似乎在沉思。1981年后画的各类荷物女,多孤独一人,或在秋风时,或在雪夜中,或在草地上,大多是拾落叶、背水、行路……她们有时变成藏女,弓身负着大木桶,在高原上跋涉着。负重女们总是身处空阔的原野,云天低垂,尘路漫漫,独立移步,艰难而无怨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5
这是少数民族风俗图画么,不是。画家在这些反复描绘的小景中暗示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感受。这感受不仅来自作为客体的彝族荷物女,也来自创作主体的深层心理。它积淀着对默默忍受命运、甘于人生艰辛的女性劳动者的一种深隐的关切和眷念。作为女性艺术家,周思聪会有关注女性的自性意识,但这似乎不是主要因素,主要因素来自她的经历、性格,尤其是早年记忆。她曾说起她的母亲——一位有文化教养,却把全部心血奉献给丈夫、孩子,默默忍受生活苦辛,以致过早地耗损了自己、悄然离世的母亲。小时的周思聪知道母亲背地里忍饥挨饿而把粮食让给他人的事情,却因为听母亲的话而为她保密。每忆及这段往事,她就有一种难言的酸苦和负疚心理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6
荷物女形象的创造,无疑与这一深埋心底的情结有关。历经人世沧桑,又经过审美的洗礼,她的寄托有了更大的普遍性,但那作品的内蕴是悲、爱、创痛、崇敬还是遗憾、喟叹,只有让细心的观者去体味了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7
毫无疑问,荷物女与周思聪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有千丝万缕的牵系。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、中年母亲、事业奋求者,她也长期负重,也曾像彝女那么劳顿、忍受和喘息,甚至也有过她们那样的木然和自足。以真诚的心画真情的画,总不免要把自己投影于作品的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8
时间距离会使人的心境变迁,映射着心境表现的作品也会变化。如荷物女,从1981年的《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》到1987年的《落木萧萧》,就有明显的不同。在前者中,人物是绝对主体,墨色凝重,其压抑还与《矿工图》有相近之处。至后者,人物变小,景色开阔起来,大块的墨团和深重调子变为淡墨淡色。荷物女倚树歇息,身后林木疏疏,落叶飘飞。

周思聪《秋收图》局部 – 9
在《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》这一作品中,画家集中于形象的细致刻画,实的描绘多于虚的想象;在《落木萧萧》里,画家着意于情景交融的创造,清远的回忆多于实近的描绘。一个强调直观切入的沉重感,一个则把沉重感纳入美的观照。其他晚些的作品,也增加了相对优美的、轻松的成分,出现了踏歌、采果、谈情、玩耍等欢悦的主题。如果把彝族女子系列和《矿工图》做个整体的比较,还可以看到画家心境的阶段性落差:前者的强烈、沉郁、疾痛和压抑慢慢转化为后者的平静、空漠、优雅和忧郁;夜海般沉默的悲悯变为夹着苦涩的清寂歌吟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名人字画网 » 从周思聪《秋收图》来看她笔下的彝族女子
 名人字画网
名人字画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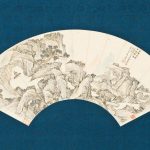 文鼎《山水扇面》欣赏
文鼎《山水扇面》欣赏 一山一宁《松下达摩图》欣赏
一山一宁《松下达摩图》欣赏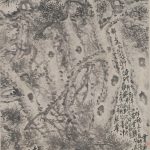 李鳝《五松图》欣赏
李鳝《五松图》欣赏 翁雒作品《耕烟翁画像》欣赏
翁雒作品《耕烟翁画像》欣赏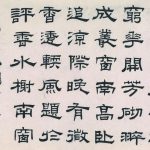 黄乐之《隶书图》欣赏
黄乐之《隶书图》欣赏 蒋廷锡《太平楼阁图》欣赏
蒋廷锡《太平楼阁图》欣赏 吕纪《四季花鸟图》欣赏
吕纪《四季花鸟图》欣赏 清代胡焕《松荫图》欣赏
清代胡焕《松荫图》欣赏 傅抱石长卷《丽人行》,铭心经典再现!
傅抱石长卷《丽人行》,铭心经典再现! 林风眠丈二钜制《五美图》,堪称镇馆之宝!
林风眠丈二钜制《五美图》,堪称镇馆之宝! 刘海粟《黄山清凉顶》,馆级巅峰巨制
刘海粟《黄山清凉顶》,馆级巅峰巨制 潘天寿指画《晴霞》, 四屏通景且首次面世!
潘天寿指画《晴霞》, 四屏通景且首次面世!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