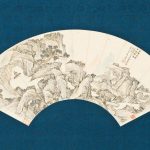吴作人是位美术教育家。“在艺术上要有我,在人生观上要无我。”是他的座右铭。他的人品与他的画作一样备受推崇。他谦诚待人,淡泊明志,清操自守;但是他也往往喜欢“打”人手心,玩幽默。不过,打得很体面,让你被打了,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;甚而,有时令你肃然起敬。

社交场上,他把幽默当作漂亮的服饰
1988年,已80高龄的吴作人偕夫人萧淑芳到港举办画展,轰动香江,传媒蜂至。有人发问:“你到底是江苏人还是安徽人?”吴作人信口答曰:“我是安徽苏州人(祖籍皖,生于苏州)。”

有好事之徒想套点花边新闻,提出要采访他的私生活问题。要一位垂垂老矣的长者谈这个,谁都难以启齿,二是吴作人夫妇的人生往事都有不堪回首的心灵创口,但又不宜明言拒绝,他试图回避话锋:“我想艺术总比个人私生活重要吧?”心怀“叵测”的记者不理这块挡箭牌,突然径问:“你有几个孩子?”

睿智的吴作人,以外交辞令反击:“我家是一个变两个,两个变四个,四个变六个。六个现时有三个在香港。”他以绕口令的速度,疾速飞“变”,逗得全场大笑,连夫人萧淑芳也忍俊不禁。谁能说他说的不对?从单身到娶妻;生女,女结婚;女婚后生两个子女,其时,女婿商玉生正陪同他们夫妇一道在港。无懈可击,一展大家风范。
世人评说吴作人的画“落笔惊风雨,画成泣鬼神。”其笔墨传情,已达出神入化之境。鉴此,吴作人成了“唐僧”,各色“画蚊子”都想来咬一口。

吴作人为人平和,朋友索画,只要得便,他总慷慨相赠,而有些陌生人想通过朋友作跳板求画,他只能拱手抱歉了。为不伤感情,他以话中递话的方式,让对方很体面地“就此留步”。一次,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位他的朋友,亮言求画。吴作人权当没听见,说:“让我讲个阿凡提做羊肉汤的故事给你们听。”大家洗耳恭听。

他说:“上传阿凡提善做羊肉汤,味美绝伦。一位朋友慕名而来,阿凡提亲自下厨侍奉。朋友吃后赞不绝口。第二天,这位朋友又带来一位他的朋友,要求品尝。阿凡提在昨日剩汤中加了一桶冷水,烧热后奉上。朋友喝了问道,‘怎么不是昨天的味道了?’阿凡提笑着答道:‘今天来的是朋友的朋友,我端的是汤的汤。’”尽在不言中,众人一笑了之,再也不提求画的事了。
生活上,他用幽默增添情趣
社交场上,吴作人以幽默作手段,坚守操节,捍卫心中一方净土。在生活上,对亲人、对朋友,他用幽默增添人生的乐趣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吴作人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、印度时,夫人萧淑芳要到农村参加土改。离别时,萧淑芳有点淡淡的离愁。吴作人宽慰萧淑芳:“你参加土改,我出国访问。我们暂且是一土一洋。”小小的幽默,将别绪离愁冲得烟消云散。

1996年苏州筹建“吴作人艺术馆”,苏州方面派人进京拜访,拟请吴作人届时光临开幕式,当时吴作人的健康状况已不能远行,只能派代表。子女们都说萧淑芳是当然代表。吴作人指着夫人说:“她办事,我放心。”一句套用毛泽东的话,博得满堂彩。

六十年代,一位长期在边远地区的老学生要出国访问。临行时拜访吴作人,闲谈中说他穿西装还不会打领带。吴作人说我教你,一边手把手地教他,一边幽他一默:“也难怪,你没当过少先队员;其实打领带就和少先队员系红领巾一样。”

八十年代初,吴作人在北戴河休养,结识毗邻的一位朋友,谈画、论艺很投契。某日兴起,吴作人带着他的外孙、外孙女突然去造访,门扉久叩不开,便留条写道:“走访不晤为怅,明午11时30分请来118,我们一块进午餐,盼勿却。”落款为:“作人等三人及小兵二人。”童心不泯。这张小便条,被那位友人视为家珍珍藏着。

曾有一位记者问吴作人:为什么你画的骆驼没有忍辱负重的压抑感艰辛感,却有一种令人充满自信、昂扬的希望感。吴作人笑着说:“预测一幅画产生的效果,比预测孕妇生男生女还难,现在还没有测试艺术家创作效果的超声波。”接着他用他的身体现状打比方:“你眼看我就要80岁了,但精神还是蛮好的,物质不行了,有心脏病,只有靠精神了。”记者顿悟,吴作人笔下的骆驼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。“情自我中来。”他总爱以幽默的方式启发对方独立思考。
 名人字画网
名人字画网
 吴作人《戈壁归驼》,精品佳作
吴作人《戈壁归驼》,精品佳作 吴作人国画《黑天鹅》,别有一番情趣
吴作人国画《黑天鹅》,别有一番情趣 吴作人先生的几件小事
吴作人先生的几件小事 吴作人手稿,功力深厚
吴作人手稿,功力深厚 画金鱼第一人吴作人作品,寥寥数笔生动传神!
画金鱼第一人吴作人作品,寥寥数笔生动传神! 吴作人国画《天高地远》,6尺
吴作人国画《天高地远》,6尺 吴作人最贵的金鱼、熊猫、骆驼和牦牛等作品分别是什么?
吴作人最贵的金鱼、熊猫、骆驼和牦牛等作品分别是什么? 吴作人萧淑芳合作作品欣赏
吴作人萧淑芳合作作品欣赏 傅抱石长卷《丽人行》,铭心经典再现!
傅抱石长卷《丽人行》,铭心经典再现! 林风眠丈二钜制《五美图》,堪称镇馆之宝!
林风眠丈二钜制《五美图》,堪称镇馆之宝! 刘海粟《黄山清凉顶》,馆级巅峰巨制
刘海粟《黄山清凉顶》,馆级巅峰巨制 潘天寿指画《晴霞》, 四屏通景且首次面世!
潘天寿指画《晴霞》, 四屏通景且首次面世!